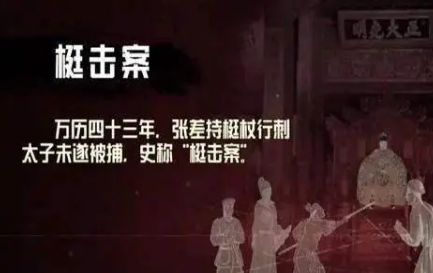
明神宗意图废长立幼,引发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
正所谓“太子者,国之根本”,册立太子往往都是影响朝局稳定的大事,虽然明朝曾多次出现世系偏移,但其总体仍然秉承了“立嫡立长”的立储原则。然而,明神宗因无嫡子,却也不喜长子,便有了废长立幼的想法,结果就此引发了长达十五年的“国本之争”。
万历九年(1581年),年仅18岁的明神宗前往慈宁宫向太后请安,一时兴起临幸了宫女王氏,因当时内有太后约束、外有张居正监督,明神宗心虚之下便不愿提及此事,但却不想王氏因此而怀孕,结果被李太后得知。鉴于皇帝始终无子,李太后非但没有深究此事,反而劝说皇帝认了临幸之事,并封王氏为恭妃。
数月后王恭妃诞下一子,取名朱常洛,由于明神宗乃是被迫接纳王氏,因而连带着对于这位长子也是极为厌恶,而王恭妃的地位和待遇,也并未因为生子而有任何提高。与之相反,万历九年(1581年)八月才选秀入宫的郑氏,则因为明神宗的宠爱,在短短三年内便先后被晋封为淑嫔、德妃、贵妃。

万历十四年(1586年)正月,郑贵妃生下朱常洵,两个月后郑氏再晋皇贵妃。正所谓爱屋及乌,由于明神宗极度宠爱郑贵妃,因而对于朱常洵也是极为宠溺。当时,由于皇后无子,按照“立嫡立长”的原则,本应立庶长子朱常洛为储君,但明神宗却开始思考废长立幼之事,就此拉开了长达十五年的“国本之争”。
很快,宫外便有了皇帝有废长立幼之心的传言,再联想到申时行在出场寻出生前请立太子被拒,王恭妃长期未获晋封等现象,这种流言立即引起了朝臣们的警觉。因此,就在郑贵妃被册封皇贵妃当天,户科给事中姜应麟、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便纷纷上书请立太子,然而此举却触怒明神宗,姜应麟因言辞激烈直接被贬为大同广昌典史。

朱翊钧的打压非但没能压制群臣,反而变相坐实了废长立幼的心思,于是吏部员外郎沈璟、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,结果两人也接连被罚。然而,明神宗此举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,大臣们纷纷上书,表示应该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,甚至有人借此抨击后宫干政,目标直指宠冠后宫的郑贵妃。
对于接连递到案前的请立奏章,明神宗朱翊钧后来干脆不再理会,眼见奏章无效,大臣们干脆将此事抬到了朝会上,此举直接导致朱翊钧一气之下,干脆连朝会也不参加了。然而,明神宗的抵触并未换来平静,朝臣们的奏折仍然不断递入内廷,甚至连皇帝的日常生活也进入了抨击之列。
结果,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交锋中,中央及地方官员三百多人参与其中,申时行、王家屏、赵志皋、王锡爵等四任内阁首辅皆因此事被迫辞退,另有一百余位大臣被罢官、廷杖、解职或发配充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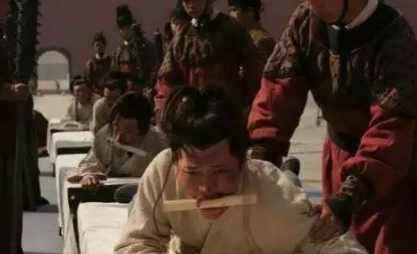
直到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,在李太后的直接干预下,明神宗这才不得不下旨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储君。与此同时,其他诸皇子也相继封王,其中朱常洵获封福王。直到此时,这场长达十五年的“国本之争”,才算短暂画上了句号。
太子遇袭导致风波再起,“梃击案”背后的复杂党争
在这场国本之争中,实际上还牵扯到了外廷的党争,由于叶向高的原因,当时朝中的东林党极力拥戴太子,而与东林党极不对付的齐楚浙党便转而支持郑贵妃和朱常洵。虽说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应该算是东林党获胜,但由于一直以来抵触皇帝,该党在朝中的势力却也是损失惨重。
